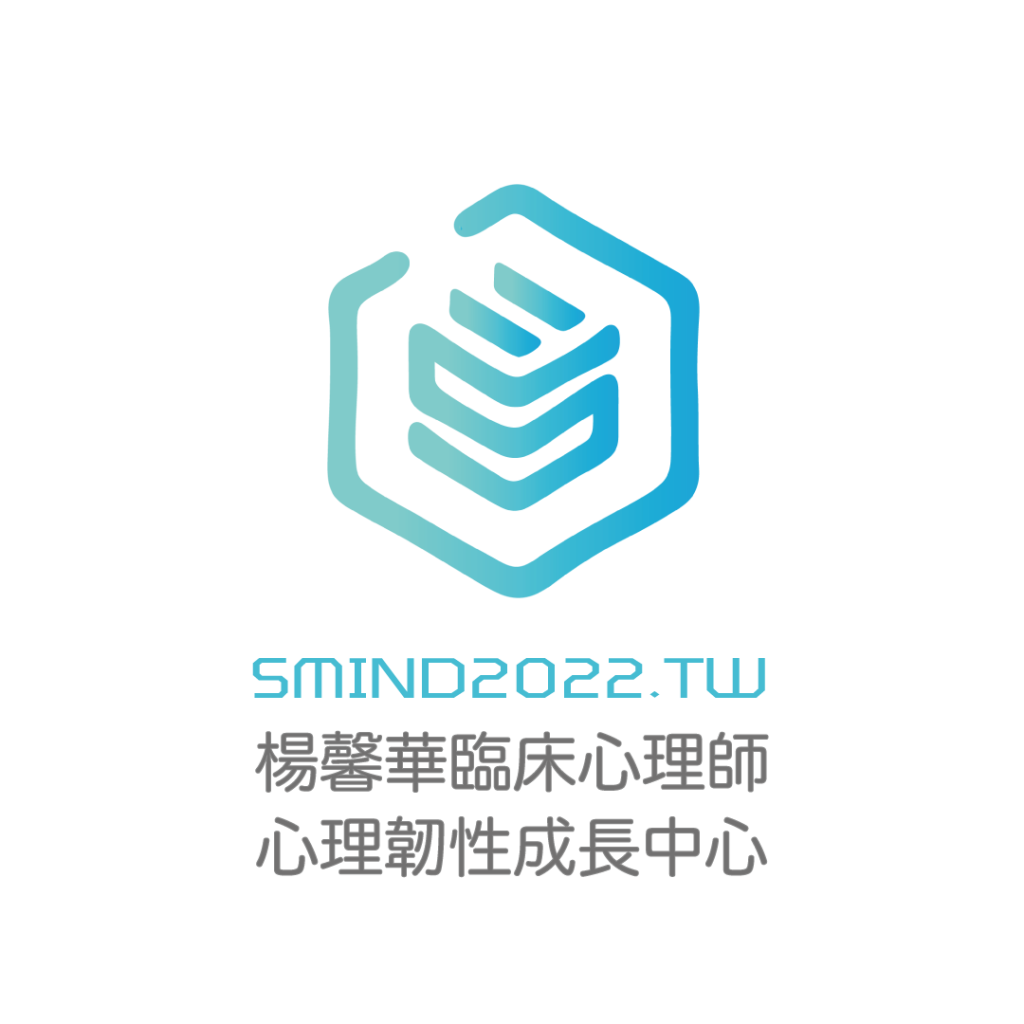在早療的領域,最心痛莫過於看見家長認為:
「我的孩子需要心理治療=心理有問題」。
楊馨華臨床心理師
家長的執迷不誤是最可怕的刀
回首我的過去生涯,前半場都在學校,不知道遇過多少家長「拒絕」孩子到輔導室,他們說的都是:「我的孩子沒有問題不用去!」,曾經還有家長隔著話筒咄咄逼人的跟我說:「老師,我警告你不要再說了(但明明就是你的小孩請我跟你說的?),我的小孩我自己清楚(他來跟我求救你有清楚?),你在說他怎樣我會跟你沒完沒了!」;掛上電話我腦海裡閃過的是他孩子那張愁眉苦臉的臉龐,眼裡閃著淚光。
於是在 2024 年 11 月三讀通過《學生輔導法》的修正案時,我高興到拍手叫好,一直歡呼。這表示未成年學生在學校接受輔導諮商時,只需要經學生本人同意並(由學校個案會議評估有需求),即可在未經法定代理人(家長)同意下執行,意思是孩子覺得自己需要輔導就可以來找老師,不需要經過家長同意。
現在我在早療領域服務0-10歲的這些孩子呢?我看見歷史,還是一樣在重演,不少的家長拒絕找心理師,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孩子沒有問題,更多家長是覺得找職能治療師也一樣。這篇文章,不是為了要掀起職能治療與心理治療師誰比較厲害,而是要告訴家長,為了什麼孩子需要心理師(不是有問題的孩子才需要上心理,我自己的孩子必上課程正是心理),心理治療≠心理有病,這篇文章是希望家長不要再肚子痛找心臟科醫師了?
心理治療師與職能治療師的差異

7 歲男孩 A,學校老師回報上課注意力分散、數學成績下降且常在操場與同學起爭執。家長帶孩子到兒童發展評估。當天安排了「拼圖+角色扮演遊戲」的活動觀察,分別由職能治療師與臨床心理師進行15–20分鐘的觀察與短介入。
職能治療師(OT)的觀察與介入重點: 注意孩子的手眼協調、抓握策略、完成工作(persistence)、在遊戲中的自我調節(例如情緒失控時是否需要外在提示)、活動分段、如何把活動拆解成可執行步驟,並給出改良建議(例如把拼圖換成較大塊、加入節奏提示、練習等待輪流)。最後 OT 設計了連續三週的功能性訓練計劃,目標是改善操作耐心與課堂作業完成度。
臨床心理師的觀察與介入重點: 注意孩子對挫折的情緒反應(例如是否有過度焦慮或羞辱感)、認知的應對方式(孩子如何解釋失敗:是歸因為自己能力?還是外在因素?)、同理與社交線索抓取(孩子是否能解讀同伴的表情或線索)。心理師在遊戲中使用短暫的情緒標記與認知重構對話(例如「你剛剛為什麼把拼圖推開?」→ 探問內在想法與情緒),並安排後續心理治療(例如認知行為技術或社交技巧訓練)。同時安排完整的心理測驗(WISC、注意力量表、行為量表)以辨識是否存在智力差異或注意力障礙。
只看職能(OT )報告結果,會得到「動作、操作、上課完成度」的具體訓練建議;若只看心理師報告,會得到「心理動機、情緒反應、認知風格」與可能的診斷方向(例如注意力不足/焦慮傾向)的建議。若二者皆有(跨專業合作),才有機會同時改善「可見的功能問題」與「內在的認知情緒成因」,也避免把症狀單一化處理。
職能治療師也學情緒,但心理治療師能做得更專業
 (A)訓練背景與專業焦點不同(關鍵)
(A)訓練背景與專業焦點不同(關鍵)
- 職能治療(OT):通常以大學職能治療系訓練為基礎就能國考,重視活動分析、功能性獨立、感覺統合、日常生活技能與社會參與。OT 的技術擅長把「治療」嵌入活動(activity-based intervention),在精神科/兒童領域常做團體治療、功能訓練與環境調整。
- 心理師(臨床/諮商):臨床心理師一定要有進階研究所訓練才能國考,學習心理測驗、心理診斷、心理治療理論(精神動力、認知行為、家庭治療等)以及長程個別治療的技能。心理師接受的測驗訓練(包括施測、評分、解釋、報告撰寫)是其核心能力之一。
雖然 OT 可以做情緒調節練習與支持,但心理師在「心理概念化」(case formulation)、標準化心理測驗施測與解釋、以及深層心理治療技術上有更完整、系統的訓練,因此當問題牽涉到診斷、智力/認知差異判別、或需要長期心理治療時,心理師的專業不可或缺。
 (B)測驗工具與診斷能力
(B)測驗工具與診斷能力
標準化智力測驗(WISC、WAIS 等)與注意力、執行功能量表,是用來判斷智能水平、發展差異、以及制定教育/治療建議的關鍵工具。這些測驗的施測、有效性判讀與報告撰寫,通常由臨床心理師負責,其施測資格與專業解釋在醫療機構中被視為專業責任。法律與專業討論也常指出智力測驗應由臨床心理師在醫療場域中施測與解釋。
 (C)介入目標不同:功能與內在
(C)介入目標不同:功能與內在
- 職能師OT 著重「做得到」與「在真實情境中的功能恢復」,所以會設計能直接提升學校作業完成、生活自理、社交輪流等活動的訓練。
- 心理師則同時處理「內在經驗」(情緒、信念、歸因方式、人格運作),透過談話療法、認知重塑、情緒處理等方法改變行為與認知模式。兩者目標不同,方法互補。
當問題牽涉到心理內在機制、需要診斷性評估(智力、注意力、情緒障礙)或長期心理介入時,臨床心理師的訓練與工具提供的是不可替代的價值;而 OT 則在功能重建與活動化介入上非常重要。二者最理想的模式是互補合作,而非任一方被孤立地當作「萬能解方」。
真實案例講解(去識別)
找治療師上專注力?
一位 6 歲男孩,因為「專注力不足、遊戲耐心低、常情緒失控」被轉介到 OT。在一次積木活動中,
OT 的觀察焦點是:手部精細動作如何?積木排列是否穩定?注意力是否能維持?任務切分能力如何?
心理師的觀察則完全不同:孩子如何處理挫折?是因害怕失敗而逃避?還是因自我效能低?情緒是如何累積與爆發的?他期待大人如何回應?積木倒下時,他的「自我對話」是什麼?
兩種治療師兩種目的:
OT 看的是功能 (function); 心理師看的是心智 (mind)。楊馨華臨床心理師
找治療師上認知?
許多家長以為 OT 的認知課程就是「注意力訓練」「思考訓練」,但心理師也會做注意力訓練,那差異在哪裡?
 1. OT 的「認知」本質上是功能導向
1. OT 的「認知」本質上是功能導向
根據美國職能治療學會(AOTA)的定義(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2020),
OT 的認知訓練主要聚焦:任務操作、動作 & 感覺整合、執行功能的外在行為(如工作記憶、轉換、計畫)日常生活技能的效率提升
OT 在意的是:孩子在任務中的表現是否更順利。
 2. 心理師的認知介入是「心智結構導向」
2. 心理師的認知介入是「心智結構導向」
心理師的「認知」介入依據 Beck 的認知模型(Beck, 2011)與後設認知理論(Wells, 2009),關注的是:孩子如何理解事件他用什麼方式解釋失敗他的自我概念如何影響情緒內在對話(inner speech)是否偏向負向心智理論、信念、動機、心理韌性。
心理師關心的是:孩子在過程中正在形成什麼樣的心理模式?這會深刻影響他之後的情緒調節、人際互動、學習動機、自我價值,這些都是 OT 無法介入的深度。
心理師處理OT沒辦法做的「根源層級」
OT 讓外在行為變好,心理師讓內在心智變強。
兩者缺一不可,但家長常忽略心理治療的重要性。楊馨華臨床心理師
心理師可以進行完整的心理與認知結構評估心理師接受完整的心理測驗訓練,包括:智力測驗(如 WISC-V)、注意力測驗、執行功能量表、情緒行為量表、人格測驗;這些測驗不只是分數,而是能看到:語文理解 vs. 視覺空間能力、流體推理的優勢與盲點、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的差距、哪個能力是真正影響孩子情緒與專注的源頭、孩子是否具有特定的心理脆弱性(如高敏感、完美主義、自我效能低落),心理師可透過標準化工具更準確地預測學習問題與情緒問題的走向(Weiss et al., 2013)。OT 雖可做基本評估,但在「心理結構」「心智模式」的評量上,並未接受同等深度訓練。
且文獻中明確指出:情緒調節與後設認知是 學習與人際功能的核心預測因子(Zelazo & Lyons, 2012)。心理治療能透過情緒覺察、認知重組、親職合作介入孩子的深層心理結構(Kazdin, 2008)。OT 的介入對情緒有幫助,但其主要效益仍集中在「行為表現」而非「內在心智架構」(Dunn, 2017)。
不找心理師,錯失成長契機
OT 能協助孩子更有效率地做事,但心理治療能協助孩子更有效率地理解自己、調節情緒、建立韌性。研究顯示,透過心理治療建立的後設認知與心理韌性,可以讓孩子在面對壓力時:更快恢復、更能自我調節、更不依賴外部指令、更能自我理解與反思(Felver et al., 2016)
這些能力將影響他一生。這些深層能力,OT 的框架之中不會訓練。OT是在強化功能與任務表現(外在),心理師則強化情緒、心智結構、自我覺察(內在)。孩子不只是需要「會做事」,他們更需要「懂自己、能調節、能有韌性」。這些是心理治療師最核心的價值,也是 OT 無法取代的。這也是為什麼我敢說,只找職能治療師會是一種損失。
Reference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2020). Occupational therapy practice framework: Domain and process(4th ed.).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74(Supplement_2), 7412410010.
Beck, J. S. (2011).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Basics and beyond (2nd ed.). Guilford Press.
Dunn, W. (2017). The impact of sensory processing abilities on the daily lives of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A conceptual model. Infants & Young Children, 20(1), 84–101.
Felver, J. C., Celis-de Hoyos, C. E., Tezanos, K., & Singh, N. N. (2016).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for youth in school settings. Mindfulness, 7(1), 34–45.
Kazdin, A. E. (2008). Evidence-based treatment and practice: New opportunities to bridge clin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3), 146–159.
Weiss, L. G., Saklofske, D. H., Holdnack, J. A., & Prifitera, A. (2013). WISC‐V Clinical Use and Interpretation. Academic Press.
Wells, A. (2009). Metacognitive therapy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Guilford Press.
Zelazo, P. D., & Lyons, K. E. (2012).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in early childhood: A developmental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6(2), 154–160.